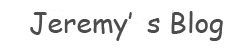蛤蟆的油
寒假回来之前,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回来看看。一本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一本是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想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因为前一阵子看了电影才知道的这本书。而另外一本是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老师的自传《蛤蟆的油》。

一开始看到这本书时还在纳闷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刚翻第一页便又有了答案:
在深山里,有一种特别的蛤蟆,它和同类相比,不仅外表更丑,而且还多长了几条腿。人们抓到它后,将其放在镜前或玻璃箱内,蛤蟆一看到自己丑陋不堪的外表,不禁吓出一身油。这种油,也是民间用来治疗烧伤烫伤的珍贵药材。晚年回首往事,黑泽明自喻是只站在镜前的蛤蟆,发现自己从前的种种不堪,吓出一身油——这油的结晶就是这部《蛤蟆的油》。
自传这个东西就是用来让别人了解自己的生活,思想和感悟。很多名人都会写自传,有的自传式人是自己动手写的;有的自传式是找人代笔写的,有的自传读起来味同嚼蜡,有的读起来让人心情顺畅,关键在于写的人将自己摆在什么位置。读这本书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和黑泽明老师面对面坐在庭院中就着一壶清酒面对面聊天。
这本书是最近看的最快看的也是最投入的一本书。文章都不长,短的就一两页纸,但是朴实的文字背后仿佛有灯光,音乐的衬托,精彩之余不留拖沓,让人回味无穷。一个自诩为少年剑客的孩子,却擅长翻绳,智力发育的比较晚以至于成年以后看弱智儿童的影片产生莫名其妙的忧郁,终于想起来原来自己小时候和那些儿童一样,在经历地震、火灾、战争、死亡,记录下挚友、良师,绘画、哥哥、剑道、戏曲、电影等等种种成长印记。 在描述这些往事时的语调是淡然平顺的,但却又充满了孩童的趣味,尤其在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第一章 酥糖与剑道》和《第二章 大正的声音》部分;但一遇到令自己懊恼或气愤的人和事情,他的真性情立刻显露无遗,透过文字,我简直能看到他在画面里挥着拳头,一边跺脚一边大喊的样子,忿忿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摘自网络书评)

读着这本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黑泽明老师言语之间透露出的谦虚,使用文字来讲故事的艺术在他手下和使用胶片似乎没有区别,信手拈来,毫无矫揉造作。在青少年时期贪婪汲取美术,音乐,文学,戏剧以及其他艺术,似乎少年时期的他就早已知道自己以后的道路,但是在回答“为什么会走上电影这条道路”这个问题时,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
这之间并非没有联系的,一直到中学毕业时,他的兴趣都在绘画和文学上,铁斋,宗达,梵高,海顿等人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住在哥哥家时,很多附近的邻居老人都是在神乐坂的曲艺场看管观众的鞋子,或者在电影院当杂役,可以弄到免票,利用邻居给的免票,整天都泡在电影院和曲艺场,对相声、评书、弹唱、鼓词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的随随便便地欣赏,却成了日后创作中难以估量的力量。然而,二十三岁那年哥哥的去世让他有了长子的觉悟,以画家作为职业是困难的,同时他也对自己是否具有画家的才能感到怀疑,才有了去应聘副导演的机会。二十六岁那年P.C.L电影制片厂招考副导演,当时P.C.L电影制片厂考试的题目是交一篇论文,以“论述并列举日本电影的根本缺陷及其纠正方法”。由于在少年时期,哥哥在电影院担任讲评人职务(无声电影时期),经常介绍好的影片给他,大量的接触电影,加之各类艺术知识的积累,使得这篇论文没有通过了考试,也标志着他正式进入电影界,成为他人生的拐角。
最后摘录一些片段:
浪费时间和金钱,人人都会,但有效地使用它,却需要才华和奋斗。自己不想前进和奋斗奋斗的家伙,即使别人死了空出位子,他也没有补这一空缺的能力。
看罢塞尚的画集,到外面就觉得外面的房屋、道路、树木都像塞尚的画一般。
看了梵.高或尤特利罗的画集之后也是如此,眼前的一切都成了梵.高、尤特利罗所画的了,仿佛从来就不是我的眼睛所看的。总之,用我自己的眼睛是看不见东西的。
现在想来,这是理所当然的。具有自己独到的眼光,那可是不简单的。
我那时还年轻,对于这一点既不满,也深感不安,于是焦急地强迫自己要有自己的看法。我看了许许多多的画展,想到日本任何一个画家都画出了独具个性的画,都有自己的眼光,因而更加焦急。
关于这一点,现在回头看一看,其实真正独具慧眼、画出自己的画的人为数甚少。除此之外,多是卖弄技巧,以此炫耀而已。
有一支歌,我记不清是谁的作品了,大意是:本来是红的,却不老实说它是红的,等到能坦率说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年。
父亲告诫我:“不要着急,也没有着急的必要。” 他还说:“要等下去,前进的道路自然会打开的。”
山顶的风终于吹到我的脸上。
我所说的山顶的风,是指长时间艰苦地走山道的人,快到山顶时能感到迎面吹来凉爽的风。这风一吹到脸上,登山者就知道快到山顶了。他将站在这山之巅,极目千里,一切景物尽收眼底。
山本先生坐在摄影机旁边的椅子上,我站在他身后。此时此刻感慨万千,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我好不容易站在这里了!
山本先生现在做的工作才是我真正想干的工作。
我好不容易爬上了山顶。
山顶的前面,就是极目千里的广阔天地和一条笔直的大道。
我规规矩矩地坐起来,而且一直规规矩矩地坐到山本先生读完我的剧本。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忘记山本先生那时的背影,以及翻稿纸的声音。
那时,我三十二岁。
我应该攀上绝顶的高山,然后如今只是好不容易到达了山麓,站在这里仰望着山巅。
我看着电视采访,心想,这才是真正的《罗生门》!
当时我的感觉是,《罗生门》里描写的人性中可悲的一个侧面,就这么就出现在眼前。
人是很难如实地谈论自己的。
人总是本能地美化自己——这一点,我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然而我却不能耻笑这位经理。
我写的类似自传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老老实实写了我自己呢?
难道不是同样没有触及丑陋的部分,把自己或多或少地美化了吗?
我在写《罗生门》这一节的过程中,不能不对比有所反省。
所以,也不能继续写下去了。
出乎意料,《罗生门》成了使我这个电影人走向世界的大门,可是写自传的我却不能穿过这个门再向前进了。
不过,我觉得这也好。
从《罗生门》以后我的作品的人物中,去认识《罗生门》以后的我,我认为这样最自然,也最合适。
人不会老老实实的说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常常假托别人才能老老实实的谈自己。
因为,再也没有比作者的作品能更好地说明作者的了。